盐的味道(节选)-九游会论坛
“不吃盐巴活不了命,不唱古歌不明事理”,是一句傈僳族谚语。盐犹如人类的血,生而必需。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市井流氓,无论王侯将相抑或在野诸侯,无论静修深山还是浮游尘世,无论愤世嫉俗还是超尘脱世,但凡只要是人,要活着,都离不开盐。也许一日三餐可以少了美酒佳肴,可一旦缺了盐,即便山珍海味也会索然寡淡。你可以视金钱如粪土,但永远无法忽视盐的存在。关于人与盐的关系,表面看起来似乎只是吃与被吃的关系。但要命的是盐这种看起来普通的东西,一旦离它十天半月,人们便会浑身无力,乃至身体变异,重至危及生命。不只是人,那些奔命于长山大野的牲畜若想要长得强壮一些,也得定期尝一尝盐的味道。也就是说,离了它不行。更要命的是,盐这种人类无法缺少的东西,不像诸如牛马猪羊、稻谷玉米、荞麦青菜、大豆高粱等等生长在大地表面供人活命的食材。盐的外形有时候是石头,有时候是一种水,它不仅没有常形,人们无法像种庄稼那样把它种出来。它也不像人类离不开的另一种物质——水,人们很难在地表轻易找到它。而盐是支撑生命的重要部分,无人能离它而活。因为在苍茫大地上总是难觅其踪,即便找到了盐矿,开采加工的过程充满危险和挑战,盐因此成为历朝历代的稀缺之物。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在滇西北江河奔流、群山耸立的横断山区,上苍恩赐人类的盐井、盐矿、盐泉在长河东西、大江南北星罗棋布。当地土著白族、傈僳族、藏族、纳西族的先民们在秦汉时期乃至更遥远的年代,通过羊、牛、马,乃至山驴、麂子等家畜或野兽的怪异行为先后发现了盐泉、卤水、岩盐的存在。这些土著部落想尽各种办法获取它,并试图占为己有。在人类的童年时期,他们通过砍柴烧火,在石板上炙烤盐水的原始手段获得食盐;又经历烧炭、泼盐水、刮盐的过程;最终学会掘井、汲卤、煎盐的手艺。澜沧江水系的这些盐点,成为日后分布于洱海周围土著部落中的 “云龙井”“乔后井”和“弥沙井”,以及兰州境内的“老姆井”“下井”“兴井”“温井”“上井”“小盐井”“高轩井”“喇鸡鸣井”“期井”等大小不一的盐井群落。后来,盐一度成为通行于滇西北的最坚挺的货币,变成可以通用于不同种族、不同部落之间交换物品的衡度。
随着盐的开采,围绕滇西北的这些盐井曾经形成过宏大的商品贸易和交通网络。当时盐的山地运输主要由马匹和人力完成,这些货物交换网络和通道也因而被称为“盐马道”,其规模和影响几乎与“茶马古道”相媲美。丰富的盐矿促成了四通八达的盐商通道,加之地理位置东可至巴蜀、西可达印度,北可上西藏、南可下中南半岛,滇西北的盐曾经围绕大理形成过盛极一时的经济和文化辐射圈,其中尤以澜沧江东岸的兰州(今兰坪)誉满全滇,被称为兰州盐。白色的兰州盐,沿着状如蛛网的盐道源源不断进入千门万户,又把成批的金银土产运回兰州,兰州因此成为滇西土著部族神往和梦想的富裕之境。
千百年来,如今籍籍无名的兰坪充满各种各样的诱惑,牵动着几代滇西北土著部落和外来移民的爱恨情仇。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曾经象征时尚、富足和前卫的滇西北地名,也意味着黑暗、血色、暴力、艰难困苦和九死一生。有人曾经在那里飞黄腾达,也有人曾经在那里身败名裂,有人在那里实现辉煌理想,也有人从那里落荒而逃。这一切,皆因兰坪得天地垂青,孕育了丰富的盐矿。白色的盐,仿佛闪光的钻石令人垂涎,谁控制了它,就控制了财富,谁控制了它,谁就控制了人。苦涩的盐,有着诸多令人熟悉和陌生的面孔。
盐是无形的江湖,由于它蕴含着可以持久坐收的暴利,每个朝代,盐场主之间都会上演或明或暗的争霸战,乃至屡屡上升为氏族部落、地方政权或者国家之间的战争。在滇西北土著们薪火烧盐、随意取用发展到为了控制盐泉氏族火拼的时代,遥远的中原大地开始了关于盐的争论。漫长的争论始于春秋时期商贾出身的齐国丞相管仲与齐桓公之间一段关于如何利用盐提高国家税收的对话。齐桓公问管子:“吾欲藉于人,何如?”管子对曰:“此隐情也。”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 秦桓公的意思是为了提高财政收入,他想向人民征收人口税。管仲回答:“这无异于让人民禁闭情欲,减少婚育,最终会导致国家人口减少,实力衰弱”。齐桓公又问:“那我拿什么治理国家呢?”管仲答:“依靠大海资源成就王业的国家,应当注意盐税政策。”管仲给齐桓公算了一笔账,大概意思是“齐国人口总数千万,人人均需食盐,若使盐的价格每升增加半钱,一月可收六千万。如果向国民征收人口税,每年出生一百万人计算,每人每月征税三十钱,总数只不过三千万。如果提高食盐价格,国家在没有向任何人直接征税的情况下,每月就有六千万钱,相当于两个大国的税收。”“如果君上发令要对人口直接征税,定会引起国民反对声浪。如果实行‘官山海’之策,即使盐价提高百倍用于国家,人们也无法规避,这就是国家的理财之法。”
管仲“官山海”之策将盐存在的利益直接提出并拿出了获利的方法,被齐桓公采纳,付诸实施,果然为齐国带来滚滚财源。齐国因财力雄厚而很快强大起来,引起其他六国纷纷效仿。“官山海”之策此后成为封建统治者重要的税课和控制手段,历久不衰,这就是盐铁榷税的开始。但是“官山海”之策倡导的盐铁榷税、官营专卖措施,存在官吏强征强买、因垄断而导致物价上涨、奸商囤积居奇等问题,其结果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并没有实现朝廷所期待的均衡劳逸、方便贡输的效果。公元前81年,西汉主政的大司马霍光受谏召开了“盐铁议会”,盐铁议会自二月开始,至七月结束。参加盐铁议会的一方为朝廷指定的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属员史和御史大夫、属员御史等。另一方则是民间推举的贤良、文学共六十余人。贤良、文学尖锐批评了西汉的盐铁官营专卖和均输制度:“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又说:“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 认为盐铁官营专卖导致国家以财利为政,与礼义立国不符。桑弘羊反驳:“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认为盐铁官营专卖是朝廷为解决征讨匈奴费用而采取的经济政策,废除则将导致边境军费不足,影响完成汉武帝未竟的外伐四夷大业。贤良、文学则将治国提升到道德教化的高度,说:“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桑弘羊列举现实问题,说:“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厉中国,杀伐郡、县、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轨,宜诛讨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赡,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纵难被坚执锐,有北面复匈奴之志,又欲罢盐、铁、均输,扰边用,损武略,无忧边之心,于其义未便也。”
代表朝廷的桑弘羊和代表民间的贤良文学由此展开激辩,论战双方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老子、孔子到管子之言,从民生、军事到意识形态,从政治到哲学,从商汤到荆轲,从就事论事到互相讥讽,长达百万言。政客的治国之术、逻辑思维与贤良文学的浪漫情怀、公平主义思想相互碰撞,谁也说服不了谁。五个月后,“公卿愀然,寂若无人。遂罢议止词。”一场历史上最长的议会结束。论战的最终结果是汉昭帝刘弗陵仅仅罢除了酒类专营和关内铁的均输官,似是无果而终。而双方的辩论记录后来经桓宽整理成书六十篇流传后世,就是著名的《盐铁论》。
在中原地区展开盐铁榷税争论的时代,滇西北土著对盐泉、盐井的争夺、统一以及对制盐方法的认识利用能力也在不断进步。汉武帝开西南夷后,至东汉时郑纯就任永昌郡(今云南保山)太守,与当地土著哀牢夷人首领商讨后,盟誓约定“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解,以为常赋,夷俗安之”,首开云南向朝廷贡盐先河。由于当时永昌郡所属比苏县(今大理州云龙县)有五地产盐,想必“邑豪岁贡盐一解”并不算重,所以“夷俗安之” 。说明西汉“盐铁议会”的结果作为一种封建政权统治手段已经辐射到云南极边之地。但由于云南盐资源丰富,加之当时行政效率不高,盐铁榷税政策并没有对滇西北土著民族的生存造成重大的影响。
至唐朝初年,傈僳族先民施蛮和顺蛮围绕滇西北洱海周围形成了大小不一的众多氏族部落。浪穹诏部落族民顺蛮在洱海西北发现了一口盐井,其王傍弥潜宗族控制了它,并将这口盐井打上了部落王族的标志,被命名为“傍弥潜井”,施蛮拥有洱海北部剑川的沙追井。除此之外,还有若耶井、讳溺井、罗苴井等盐井。虽然各部落拥有规模不同的盐井,但他们并没有将食盐与部落王族的利益联系起来,“当土诸蛮”用“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的古老方式“自取食之,未经榷税”。当时洱海周围较大的几个部落,即“诏”都有氏族或联姻关系,如浪穹诏与邆赕诏诏主是兄弟关系,浪穹诏主与蒙舍诏主又是甥舅关系等,各诏以洱海为中心分布四方,实力相当,谁也吞并不了谁。
吐蕃兴起,与唐朝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尽管当时盐并不是双方的主要目标,但是滇西北重要的战略位置成为双方争夺的要地之一。生活在滇西北的傈僳族先民陷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战乱。崛起的吐蕃从沿澜沧江两岸不断南进的同时,约公元690年架通了滇西北金沙江上的神川铁桥,成为进入云南的重要通道,长安三年(703年),吐蕃赞普犀都松率军攻克降域 ,“及至兔年(703年)冬,赞普赴南诏,攻克之。” “及至龙年(704年),赞普牙帐赴蛮地,薨”。尽管吐蕃赞普犀都松死于洱海北部,但他的军队仍然控制了洱海西部云龙、兰州一带的盐矿,并且在苍山西麓的漾水、濞水上修建两座铁桥,“以通西洱河蛮、筑城镇之”。吐蕃在洱海周围的土著部落中封了六、七个王羁縻管制,“使白蛮来贡赋税,收乌蛮于治下” ,属于乌蛮集团的傈僳族先民施蛮和顺蛮也节制于吐蕃铁桥节度。而此时,唐朝军队也雄踞洱海东北部的剑南和姚州,形成犄角之势,与吐蕃的滇西北争夺战势不可免。当赞普南征身殆的消息传到都城逻些 ,吐蕃内部豪族发生骚动,附国尼泊尔公开叛乱,整个吐蕃出现了严重危机。出于稳定政局的需要,已故吐蕃赞普犀都松之母尺玛蕾辅助年幼的新赞普执政,遣使到唐朝求婚,三年后,唐朝与吐蕃举行“神龙会盟”,金城公主远嫁吐蕃,双方恢复亲善关系。但是唐中宗并没有停止对滇西北的进攻,乘机命唐九征进兵洱海西部的西洱河蛮地,唐军“破之,俘虏三千计”,并焚毁了吐蕃进入西洱河的两座铁桥,“焚其二桥……建铁碑于滇池……以纪其功”,又将那里的傍弥潜盐井和傈僳族先民顺蛮族民揽入治下。
焚桥纪功也罢了,西洱河诸部落人民有盐可食,有田可耕,也在唐军抑或吐蕃的管辖下相安无事。可是此时唐朝却出了一位监察御史,名叫李知古。景云元年(710年),李知古上奏皇帝:“姚州诸蛮,先属吐蕃,请发兵击之”,他的意思是要铲除或者征服当时吐蕃麾下的那些部落。唐睿宗批准了李知古的建议,“诏发剑南募士击之”。慑于大军的武力胁迫,洱海西北部的部落相继归附唐朝。急功近利的李知古并未就此罢休,“既降,又请筑城……重税之”。不仅加重赋税,还试图奴役驱使洱海北部各部落人民建城筑池防御吐蕃。朝中黄门侍郎徐坚极力反对李知古的主张,他认为西洱河的部族在蛮荒之地,有待开化,应当采取有异于唐朝的制度进行羁縻,而非兴师动众进行远征,如果这样将得不偿失,说 “蛮夷生梗,可以羁縻得之,未同华夏之制,劳师远涉,所损不补所获。”可是唐朝皇帝并不听取他的建议,仍然“令知古发剑南兵往筑城”。洱海北部部落人民在沉重的赋税之下,又将面临抽调万人为奴参与筑城的境地。部落酋长们根本不配合唐朝的高压政策,导致李知古的命令无人听从。恼羞成怒的李知古诱杀了洱海北部影响最大的邆赕诏诏主丰咩,并将其王族子女抓为奴婢。这激起了邆赕诏、浪穹诏、施浪诏王族和族民万众的愤怒。丰咩之弟,浪穹诏主丰时为兄报仇,联络吐蕃和施浪诏、邆赕诏袭击围攻唐军,唐军溃败,死者逾千,李知古被杀,遭“断尸祭天”。西洱河诸部与吐蕃由此向东“进攻蜀汉”。导致洱海诸部“相率反叛,役徒奔溃,姚、巂路历来不通”。
唐朝内部此时也出现了危机,主要是由于依赖均田制的税收无法支撑长期与吐蕃的战争,导致财政入不敷出,开始酝酿军事与税制改革。废止百余年的盐铁榷税又提到宫廷议事,左拾遗刘彤表请实行盐铁专卖:“榷天下盐铁利, 纳之官”, “官收兴利,贸迁于人”,认为“取山海厚利, 夺丰余之人, 润穷独之谣。损有余而益不足”。他的看法与西汉时期桑弘羊的思想如出一辙。开元十年(722年)唐朝开始征收盐课,不再免税。为了强化军事组织能力,也开始了以募兵制为主的具有“兵农之分”的职业化军事改革。此后唐军卷土重来,与吐蕃争夺位于今四川省攀枝花市盐源县的“昆明城”和“盐城”,在数次争夺之后,至开元十七年(729年),“巂州都督张审素攻破蛮,拔昆明城及盐城,杀获万人” ,置“昆明军……管兵五千一百人,马二百匹”,以控制盐城一带的盐井。
在川西取得胜利之后,为了夺回滇西要塞牵制吐蕃东进,唐朝军队积极扶持居于洱海南部弱小的蒙舍诏,地处山地的蒙舍诏也对洱海西、北的湖岸良田垂涎已久,双方一拍即合。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朝派御史严正诲与南诏王皮逻阁策划进攻洱海周围最富饶的“河蛮”地区。割据洱海北部的邆赕诏、浪穹诏、施浪诏与蒙舍诏是氏族亲属联盟,在接到蒙舍诏王发兵协助的请求后,邆赕诏主咩罗皮以为可以与其舅蒙舍诏王皮逻阁共享其成,立即发兵,与蒙舍诏南北夹击,迅速占领了洱海西岸的河蛮领地,战败的河蛮王族向北迁徙,流亡浪穹诏地。战斗胜利后,蒙舍诏主皮逻阁并不想让他弱而无谋的外甥占据富饶的河蛮领地,很快率领军队把咩罗皮逐出大厘城,迫其退往洱海北部的邓川。蒙舍诏不断向洱海北部推进,与邆赕诏、浪穹诏、施浪诏反目成仇。三诏组成氏族兵团南下复仇,猛烈进攻洱海北部的上关龙口,在即将攻破龙口关时,唐朝剑南节度使王昱的援军赶到,三诏未能一鼓作气攻下龙口城。蒙舍诏反败为胜,与唐军共同出关追击,三诏联军多死于攻城之战和洱海周围的沼泽地。此时吐蕃军队却被吸引至川西,专注于防御作风彪悍的“山南兵”而无暇顾及。蒙舍诏乘胜追击,击破邆赕、浪穹、施浪三诏故地,三诏族民和其王一路向北溃退至剑川、鹤庆一带。浪穹诏主铎罗旺退保剑川,施浪诏主施望欠率领部落迂回重返牟苴河故城,试图持险拒守。不料蒙舍诏和唐朝军队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城池很快被攻破。城破后,施蛮王望欠率领一半王族绕道苍山西去永昌,却被蒙舍诏和唐军在澜沧江岸成功堵截。后来,施浪诏主不仅失去了“沙追井”等盐场和大部分领地,还不得已将自己具闭月羞花之貌的漂亮女儿“遗南”献给蒙舍诏王才得以回到洱海地区保全性命,终老于蒙舍诏的白崖城。他的弟弟施望千则率另一半族民北走吐蕃,进入剑川、铁桥一带吐蕃控制范围,被“吐蕃立为诏,有众数万”。北去的邆赕、浪穹、施浪此后被称为三浪诏,他们就是现代傈僳族所称三祖,即“部祖、施祖、迈祖”,族民施蛮和顺蛮也被称为“浪人”,就是今天傈僳族的直系祖先。
……
(《民族文学》汉文版2020年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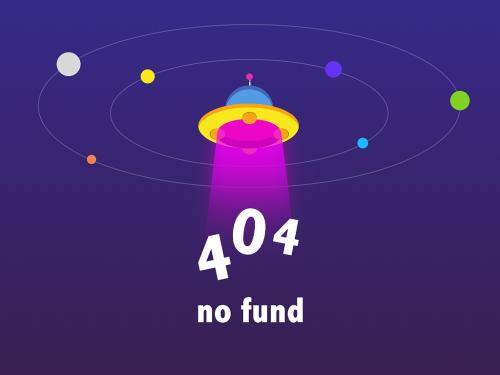

 九游会论坛的友情链接:
九游会论坛的友情链接: